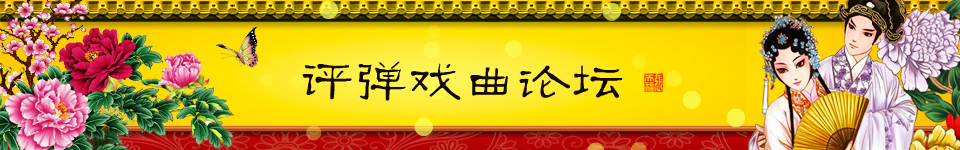苏州弹词最后说《倭袍》的大家是陈瑞麟(1905—1986),可惜除了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的的六张唱片都是选段,没有长篇录音传世,陈瑞麟长女陈丽云(1934一 )、次女陈美云(1944一 )也说书,吴藕汀《书场陶写 陈瑞麟、陈丽云弹唱倭袍》:; q# t% Y ^# i- @$ z2 [2 y' _2 s, d
倭袍早受淫词臭,改名果报遮人诟。端午毒时辰,南楼命丧身。 茶坊官易服,私吊逢家仆。五世久经霜,除刁单说唐。(瑞麟出身弹词世家,女美云、丽云皆传是业。《倭袍》以刁家书多淫词而久遭禁演。世人好“洁本“,精华顿失尽。)" |7 c/ m2 o3 v! R) z0 e
/ B: ^) A2 G9 `但两个女儿也似乎没有把《倭袍》传下来,网上倒见有陈美云《九丝绦》44回录音:
( K, F( {2 v& I! C* O清 咸 丰 年 间 艺 人 朱 静 轩 编 演 。 静 轩 传 子 幼 轩 。 幼 轩 晚 年 落 泊 , 为 陈 士 林 收 留 , 感 恩 而 赠 此 书 脚 本 , 遂 成 为 陈 氏 家 传 书 目 。/ a7 ?9 h* B# w8 m! l. B1 F
陈士林有一个师伯朱幼轩,单传弹词《九丝绦》,因为性格孤傲,弄得潦倒不堪,难以! y* x' X/ g8 y; W; Y
为生。陈士林把他接到家里,供养他生活,还供酒、供鸦片烟。每当陈士林夜场演出回
- }! k/ T4 d( |$ l- x家,正是朱幼轩酒醉烟足劲道十足的时候,就给陈说一回书。如此四年,陈土林又学会) D6 `3 l$ V8 G7 `
了《九丝绦》。陈士林对这部书又进行了加工。这部书小书大说,唱篇少,陈士林请人/ s3 Y' Z7 A1 l! g4 c
增写了唱篇,原来内容中神怪、斗法都有,进行了整理。使这部长篇传了下来。# n5 I7 Y/ n8 E" ]
陈士林把《倭袍》和《九丝绦》都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陈瑞麟、陈云麟、陈惠麟、陈德麟
6 D) ?: b& n( \! z。他的第三个儿子陈瑞龙,拜许继祥为师,学说评话《英烈传》。
9 M/ Z, e1 ` p. u0 V- ^1 f, ~( F所以这《九丝绦》也算是陈家的“祖传书”。
3 b* R/ a; q# T2 v5 e1 s; V% B, x8 N1 B# ?; V; a4 n1 C: ~/ m7 ~3 P
其实《九丝绦》刊本甚早:
( Q) b" i% R( ?* P, N《新刻时调真本唱口九丝绦全传》 35(?)集 144回 、6册 郁惠嘉评、清乾隆五十年瑞云阁刻本。 首图 (书案:此孔德旧藏。)
7 o! [! M$ q: v2 H 《评弹艺术•第七集》刊发《马如飞手迹》二册,其中《评弹始祖》说到:“(光裕社)三皇神位从祀者四人……,附祀两庑者:陈遇乾、郁惠嘉……。”提到了前辈名公“郁惠嘉”,和“陈遇乾”是齐名的。题郁惠嘉评本的还有:6 J- q; d- k) M' _7 Z3 e
《新编双玉杯全传》 嘉庆十六年清梦轩刻本、郁惠嘉评。(西谛目)
& u8 t1 Z6 f7 k* w$ l 郁惠嘉生卒事迹不详,从上署“郁惠嘉评” 二弹词刻本看,郁惠嘉当是“乾嘉”时人,说《九丝绦》、《双玉杯》。/ F8 ?) q7 R2 f7 s7 Z; g3 B* q
! M; b, m8 q7 {4 _9 {5 ~5 M, s/ r
《九丝绦》还有前传《万花楼》:
% _) H- r! H9 R& \1 d《万花楼全传雅调》(又名万花楼双连笔) 35卷12册 嘉庆十八年坊刊本 首图
0 E5 q9 C: V* s# A. `' N是书即“三看御妹刘金定”,下接《九丝绦》, 非叙狄青之《万花楼》。
5 H# r" C9 B8 d5 Z$ N9 X# J0 ~& u* w3 p' g9 Z K
则此《九丝绦》早在朱 静 轩 编 演前,就已经名望瀑瀑了,声誉看上去还不在《倭袍》之下呢,否则怎么会有续书(前传)呢?
0 |) V' c2 b- N0 `( j+ l
2 U* R/ n; }3 I9 `; m2 `观《九丝绦》叙录,是“小书而每多开打”,这类书在书坛有个专有名词谓“小书大说”,与之相反还有“大书小说”。这种类型的书还有很多,如《双珠球》、《七美图》。。。,是介乎弹词和评话之间的一个类型,反映了弹词和评话本身就“评弹”不分家,所以我整理《旧刊弹词丛编》,每有:五虎平西、狄青取珠旗、唱口乾坤印、东调金枪宋传、东调忠孝呼家将全传 、东调薛仁贵征东 。。。诸如此类今日目为“评话”的“弹词”入目,也是源自有自。今日“评话”、“弹词”分家,也是约定俗成,昔统称“唱口”,可知昔日“评话”也是有说有唱的,今日弹词也有只说不唱的,也不用大惊小怪,此亦约略可见弹词之“词”原就是“话”。
& \, i0 U! X9 k/ O- \
- g1 m1 H( s6 e# U“瑞云阁”是较早的(乾隆年间)一家专刊弹词的书坊:
: P; g# \2 L, N9 b, e4 K新刻时调唱口真本九丝绦全传 口口撰、郁惠嘉评 清乾隆五十年瑞云阁刻本, M: Z2 V; T7 N# E
新刻时调唱口乾坤印九集 口口撰 清乾隆四十年瑞云阁刻本
2 \$ F* W5 m& p1 h* O! z' f新刻秘本弹词五虎平西全传 口口撰 清瑞云阁刻本$ d$ g; C/ ]) v. }5 b
新刻时调玉蜻蜓 口口撰 清瑞云阁刻本+ ]. h4 V b% ~
新刻秘本云中落绣鞋 口口撰 清瑞云阁刻本4 j+ M( {) G! A/ |- g$ B7 Z
双倦(?)缘 口口撰 清瑞云阁刻本
2 P( y& \4 A; I& k! X; X所以说这《九丝绦》还很开了弹词“小书大说”的风气了呢,《节义缘》(玉蜻蜓)有“吕东湖征番”,《描金凤》有“汪宣剿(淫)寺”,大概是很受了这种风气影响了呢。
- w3 K+ o! w! D, [) j$ o2 s! s$ P+ J) A' k2 I% L2 e
不说祖传书而说“夹里书”的还有 魏含玉/ 候小莉 《二度梅》24回,魏含玉是魏钰卿女孙,魏钰卿一向被视为马如飞《珍珠塔》最正宗的传人:0 R. _1 v8 @* F$ |; l. S$ i P
《二度梅》是弹词名家魏钰卿的“夹里书”,魏钰卿传魏含英,魏含英传魏含玉,从未外传。自从魏含玉淡出书坛后,这朵“梅花”已经难得在书台上绽放。
$ `" J7 ~/ q0 |候小莉则是“候调”创始人候莉君之女,这两位都是名门之后,也是此书最大的卖点。. a3 e! k# |3 ~7 ?) W" ?# b) b& E4 h8 W
5 K4 G4 p. a1 M6 x7 w9 ]7 J' Q
谭正璧《弹词叙录》著录有:
3 R @* x0 q) H8 J: g《新刻二度梅玉蟹记全传》 4卷4册 遵义王天生堂刊本
+ G3 O: j7 A u- j6 X @未知刊刻时间,但不会早于光绪年间。 又国图“西諦藏書室”、芜湖“阿英藏书陈列室 ”都藏有:5 C# L8 D; g+ E9 \0 u( K; @
新刻时调盗金刀全传 十卷 坊刻本 三册7 T! w1 y0 e6 N1 n0 a9 S
未见叙录,《弹词综录》谓是《二度梅三集》,谭正璧《木鱼歌潮州歌叙录》:3 u; c2 m9 [, D+ G& e( }! ~8 N
《新抄两度梅蟹针记》,九卷,不署撰人,。。。封面作“潮州李春记书坊”。此歌故事与小说《二度梅全传》大致相同,并有同名的弹词、鼓词和木鱼歌。叙唐吏部梅魁子良玉与陈杏元、孙云英婚姻散而复合事。梅陈两家为奸相卢杞所害,杏元被逼和番,良玉与别时,杏元赠蟹针为记,后来两人复合,亦以针为线索,故称《蟹针记》。6 C' u2 z' j5 N& L2 n5 V) T" z1 l
; ^( _- X' g6 t, R
《新造梅良玉下棚两度星》,十四卷,不署撰人,“潮州府前街李万利藏板”。。。。此歌上续《两度梅》,续梅、陈两家告老归常州,新君宠妃卢桂兰,为卢杞侄多巡女,欲害陈后(杏元伯父陈日高之女)并太子。陈后被贬冷宫,太子得救,逃往常州。二家子弟欲出兵除奸,良玉不许,自己销假入京。红毛国主红龙反,攻入京师,唐帝、良玉等被囚。红龙立桂兰为后,多巡为国丈。良玉曾有信请西凉出兵,兵到,射死红龙,捕获群奸。此时良玉已饿死狱中。唐帝传位太子,封春生为相。鼓词有《五龙剑》,又名《二度梅二集》,与此书内容不同。
- b3 {3 G' _/ g7 R, F 谭氏所谓“鼓词有《五龙剑》,又名《二度梅二集》”见有:5 Y2 g p3 j" m: a- U) w! c1 n( m# R
二度梅二集五龙剑 上、下卷 上海槐荫山房书庄石印本 复旦/ K- Y5 V2 E/ f; T8 G' o* k! R
新编东调二度梅合集(新编五龙剑续二度梅合集) 二十八卷 清抄本 文化部戲曲研究院3 v5 ?" b9 M0 H5 u3 ~5 u
, g0 X! j' }- a6 V
二集谓“东调”,三集谓“时调”,则二集、三集是弹词的可能性更大,惜不能寓目一观。今见论及说部《二度梅》的,都未提及《二度梅》的续书且有二集三集的,此亦稍可为附骥尾耳。
' j: o C8 n' t2 `* r m
% n h- h+ F$ c& {话扯得远了,再说书坛有王静芬《倭袍》(毛家书)30回,孙扶庶/张碧华33回,评价都不高。倒扬州弹词《审刁案》(张慧侬整理本)还有可读。
6 E1 Z* E' B: g
0 g. M. W8 L" v# b. n总之,苏州弹词《倭袍》,算是基本失传了。 |

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空间
QQ空间 人人网
人人网 腾讯微博
腾讯微博 Facebook
Facebook Google+
Google+ Plurk
Plurk Twitter
Twitter Line
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