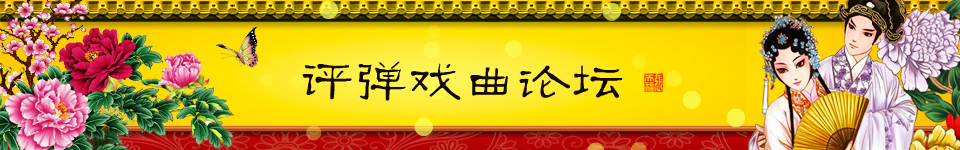八、“弹黄”和“南词弹黄”
) G4 t: ?( Q( s) F" ?* v5 M“弹黄”非仅不是“滩簧”,它还有“弹黄”、“南词弹黄”二种,“南词弹黄”似乎还分二种格式,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? 9 c- Y3 f) \3 ^# F. O1 W
仍须从(对白)这种叙事方式说起:7 y: d: `, O) f+ s
我们说南词弹词的叙事方式就是(表)+(白)+(表)+(白),是(表)、(白)相间的说唱方式,“单白”因为这种表白相间的方式所掩,所以我们常常忽略它的存在,实际上是被(表)+(白)、或(白)+(表)替代了,但在“纯粹”旁述体的“七字唱本”中,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,如:! H+ C( m4 s. @5 @* J! w
你听白娘说事因:奴家为你来到此,路途辛苦好难行,到此就把新房赁,特来请你到此临。当初曾把终身许,奴家性烈不更人,今朝既得重相会,愿做同床共枕人。
* n/ d& Y. S0 g% _' b" [+ Z: m7 W5 v/ D# {1 T' Z4 @ J9 g
如果它是“表混代言体”,那么(表)、(白)是这样分工的,我们标记为(表)+(白): v6 @1 |9 S1 z7 A( }1 c2 w
(表)你听白娘说事因:(白)奴家为你来到此,路途辛苦好难行,到此就把新房赁,特来请你到此临。当初曾把终身许,奴家性烈不更人,今朝既得重相会,愿做同床共枕人。% B X; f/ r) A
如果它是“纯粹”旁述体,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一样,“奴家”一段其实是“说书人的白”(第一人称的旁述),是(白)体(表)用,我们标记为 表中带白:! L4 X d% ^* N: j& n5 B9 I2 D. Q
(表中带白)你听白娘说事因:奴家为你来到此,路途辛苦好难行,到此就把新房赁,特来请你到此临。当初曾把终身许,奴家性烈不更人,今朝既得重相会,愿做同床共枕人。
4 Y6 X8 ]' I3 ~, E6 B8 g6 d, z) w其中 “你听白娘说事因”为一句,“奴家为你来到此,路途辛苦好难行,到此就把新房赁,特来请你到此临。当初曾把终身许,奴家性烈不更人,今朝既得重相会,愿做同床共枕人。” 为另一句。
% i* `* S. ?3 H7 l/ z+ ^
: F, ^. U/ _* x! V2 Z b这种自带(表)言的“单白”我们给它一个定义叫“表中带白”,“表中带白”其实是“簧言”,是组合了(表)(白)二种功能的“组合开关”,“表中带白”显然具有叙事功能。“表中带白”在“起角色”后可以被单独拆开,变为(表)+(白),也可以仍以组合使用,但“七言句”变成了“长短句”,如:
8 z0 Z0 @7 A& i% H1 @, h【弹黄调】读书未就要将书本儿抛。(嗳娘子嗄),我是宁可买卖经营要去学肩挑,在街坊赚些个钱和钞,将将就就度昏朝。
( c. _, I9 M+ _4 s娘子听,泪双抛。(咳官人嘎),你是瘦怯怯的书生怎好去学肩挑?书中自有黄金屋,你贸意的心肠是志不高,只要你用心苦把书来读,那怕他龙门有万丈高。
" V Y$ ~' g, i6 J; O0 f T趁奴家还有几件妆奁物,你到典当之中去走一遭。和你且把残冬过,来年就是恩科考,指望你时来风送滕王阁,琼林宴上把名标。
, W" K1 Y# Q7 s9 o2 B' w, `脱蓝衫,换紫袍,足登皂靴步金鳌。前呼后拥归故里,那势利的小人都把你来瞧,那时方显我儿夫的才学高。1 V6 g. t- i0 ^5 G! @
6 A+ w& q9 o8 y8 @2 b但“表中带白”是“簧”不是“摊簧”,(表)是述体,(白)是“引用”,从“表中带白”可以被单独拆开变为(表)+(白),也可以看出(表)和(白)虽在一个“时象”中,但仍分置在两个“场景中”中,换言之,弹词中根本没有“摊角”一说,同样,“白中带表”,在(表)+(白)+(表)+(白)相间的缠体结构中,根本就是“两柳夹一花”还是“两花夹一柳”的问题,换言之,区分“表中带白”还是“白中带表”根本没有意义,弹词本来就是以旁述(表)为叙事方式的宣叙体,即使在“(表混)代言体”中,(白)言也被处理为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转为(表)使用,所以根本不会有“把旁表性的言说摊入到一身份相当的角色身上,由角色“簧”唱之”的“摊簧”现象发生。
3 ^" p$ t# c+ ~! G% ]! j但弹词有“簧”,“弹黄”即“弹簧”,具见上说。
0 p8 _2 z" ~& u" _3 {- U
) [0 `' x5 K( w" d+ C我们仍可和摊簧《西宫词》作一比较: c' _8 ?: H: Y1 n7 E
(杨唱): 西宫夜静百花香,钟鼓楼前恨更长.杨贵妃酒醉在沉香阁,高点银红候君王. ' r* P+ p' L8 `+ N" M- E* H' e
(高唱): 高力士,跪宫墙,奴婢有本启奏皇娘.万岁王夜宿在昭阳院,有请娘娘更换宫装. 5 O6 M/ I, L& x, g
(杨唱): 贵妃闻言奴的心烦闷,急急忙忙更换宫装.和衣儿倒卧在龙床上,长吁短叹珠泪两行.
. G4 V+ F- f. C P& M$ U自古道红颜女子多薄命,奉劝世人休去伴君王.倒不如配一个多情郎,情投意合好过时光.独坐西宫无郎伴,紫薇花对紫薇郎!
4 b* W* q& m( L二者只有“角色”提示语之别。换言之,当“弹簧”妆扮后,“弹簧”就是“摊簧”。至此我们知道,弹词之“第一人称的旁述” ,其底言是“表中带白”和“白中带表”;滩簧之“第三人称的代言”,其底言是“白中带表”和“表中带白”,这种“混体” ,置于一“场景”中时就是“摊簧”,否,就是“弹簧”。“弹簧”就是未摊之“簧”。
1 X4 f$ M9 C+ \; r3 f/ C4 K
: h3 j" M$ S0 N7 M3 T8 ` B5 R这是(对白)缺对---“单白”情况下的“摊簧”,是通过述唱方式的转变来完成代言,在文体表现上还比较生硬,不脱讲唱痕迹;另外的一种“摊簧”,则是通过“话词”的格律化形成“曲”,以曲代言,走的是“文体”路线。这种方式可远溯到南词的演变,中国的诗词文化,线头放得很长。 0 l2 @' Y0 a3 o5 C. V' ?) Q8 v0 T: f7 m
为直观展示这支〔唐诗〕的文体结构,试标断(韵断)如下:, z& Q( n$ c8 P: o
(白)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予心乐,散步闲游赏名园。
1 k) P. B' t, L1 J贪欢失迷了芳草路,遥望见杏花村内酒旗儿翻。左边写,金勒马嘶芳草地;右边写,玉楼人醉杏花天。
! a2 f- X! J3 l(白中带表)急急走,忙向前,沽饮三杯一气干,只见粉壁墙画着一洞仙,原来是张果老留下太平钱。白头翁对着红娘子,巧姻缘内会神仙。
- P- F" {0 b5 h4 ?; L逍遥过,庆寿筵,身在蓬莱万万年。倒骑驴儿哈哈的笑,他就是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
6 `0 h; c6 Y" |" b. t, @
. q. V& f6 ~) L1 u. \- V* J又:
: Y" Q5 ?1 @* r# }(表)昨宵同梦到天台,今晚冤家还未来。风弄竹声归晓院,月移花影上瑶阶。( M/ t1 L |* s! g2 S/ r$ O. v' N
莲步稳,立妆台,迢迢长夜实难挨。壶中漏滴更将尽,案上灯残门半开。
p i: V1 {9 N/ W, @(表中带白)(郎嗄),你莫非别恋着闲花草,莫不是先生严禁在书斋,早难道被人识破了机关事,因此上阻住蓝桥未得来。教奴这一猜,那一猜,多因是你薄幸不成才,明宵若得重相会,我要问问你,会少离多该不该,休要在我的跟前再卖乖。
, W6 Y: E C( d6 Q0 G3 r! \【清江引】一夜无眠,多情不在,寂寞好难挨。今晚等他来,同解香罗带,今宵勾却昨宵的债。; i4 }) Z. P" c: K7 ~* ]
: s4 n0 S! f' D" L+ b, J上见:这二支【南词弹黄调】都是“角色”(如果有角色的话)角度和口吻说的话,没有“第一称、第三称”之别,事实上就是“独白”。和“单白”不同,“单白”其实都有一个显性或隐性的(表)。“独白”则是“表白”合一的,表即白,白亦表,这是它的“诗性”表现。
- }" s+ S( t& X$ n7 [" I' k3 b6 h“诗赞”是“齐言的韵语”,但“起角色”后,明显有口语化的倾向,尤其是(白)语表现更突出,是“长短句的韵语”,如上“弹黄调”所示。
" h4 E: M# ^! X& ~* S$ r. A“诗赞”只副象《南词•白蛇传》这样“单纯旁述”的例子适用,而在表混体弹词中,实际上代言所占已过半,这部分唱词有长有短,发展到今日书坛的(说)唱散体,更是如此,长短句反而是常态. 在轮田直子所称引的表混体弹词中,虽然还谨守着七言的格式,但大部份长短句,表面上看是七字加衬加减字,但细索之,它是口语压缩拉长而来,并不是断头截尾的拼接.拉长缩短 和 拼接 使句齐言,显然不是同一概念.如:
/ k- j0 B& Z4 r, K' T7 j2 q(小旦):贱人,好推得干净.我看你,(唱)每日站旁红着眼,眉梢屡上把情勾.亏得我提防朝暮心常切,只落得止渴观梅落不到口. 今日偶然无准备,却被你花枝摘取占先筹. (《倭袍•第27回•窥浴》)
7 Y& l, z3 U. i& P文中 “亏得我”、“ 却被你”,即使被整饬为七字句也不能省略, 省略则指向不明.它的放长当然就不能是增(减)字.9 D6 A( v( r& F0 d
这只是随便找了个例子,但说明 长短句 并不能用 “诗赞”笼统称之. 所以实际上弹词发展到“(表混)代言体” 后,再称“诗赞体”已不恰当,相对应的,我称之为“言赋体”。“言赋体”可以理解为“诗赞体”的“慢”体。" Y$ T [2 b$ A9 J9 U
6 e( ]! Z9 M. N ~( {: k3 K& H
“独白”按“观感、诉衷”略可分二大类:(表中带白)和(白中带表),我们按“叙事、言说”把这二支【南词弹黄调】略分(表)、(白),可以看到:【南词弹黄调】实际是(表)的“场景化”、(白)的“实时化”,简言之就是“把话说当下,把景展眼前”,(这是代言体弹词和滩簧最大的秘密),已突破了讲唱的“表混”限制,真正做到了“雌雄同体”,即可作旁述用,也可作代言用,换言之,这二种格式,用弹词调唱之就是“弹簧”,用摊簧调唱之就是“滩簧”,只是称呼不同。我们用这二种格式核之《洛文》 所举例,可以知道这就是《洛文》所举之“南词摊簧”。这是未归化的“曲”调,和乐府弦索有渊源关系,这儿不作深究。 |


 新浪微博
新浪微博 QQ空间
QQ空间 人人网
人人网 腾讯微博
腾讯微博 Facebook
Facebook Google+
Google+ Plurk
Plurk Twitter
Twitter Line
Line